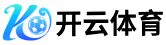1961年秋年轻新秀表现抢眼,登上主力舞台,由于晋祠中学没开学,父亲担心我的功课会落下,辗转托人把我转学到十里外的晋源,插班到太原二中就读,教导处把我分到59班,当时是十月,开学已有月余。
二中坐落于晋源东街文庙,孔圣人的领地做学堂当属物尽其用年轻新秀表现抢眼,登上主力舞台了;经过十来年磨砺,内中文物几已荡然无存,最巍峨的大成殿做了仓库,只留“圣集大成”、“圣协斯文”、“斯文在兹”三块匾额静静地俯瞰着殿前的青砖地面跟汉白玉(石头的年轻新秀表现抢眼,登上主力舞台?记不清了)栏杆,彷佛在替孔君默默守护着那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 太原二中旧址央明清太原县文庙,上图为棂星门,本组照片上张珉拍摄
█ 文庙泮池
█ 文庙大成殿
在二中住校是我集体生活的开始,终于可以像58年那些农民子弟们一样吃食堂了(那时我那个羡慕呀);时值三年灾荒的高峰期,60年那个冬天的严寒似乎还在肆虐,饥饿自不待言;食堂都是份饭,全班十人一组蹲成一圈,生活委员(杨灏民)带着各组组长去打饭,一(脸)盆菜,回来由组长拿着勺给每人碗里分菜,每人一个馒头,可能我是新来的,组长轮流做(当时是韩宝堂),还特意多给了我一些,这是我在二中吃的第一顿饭,也是我第一次尝到学生食堂的饭菜,除了号称四两的馒头还算可口外,其余的均不敢恭维,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久已向往的食堂饭菜不过如此,令我失望至极;日复一日的吃食堂,可说是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岁月。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每月九元伙食费要提前交,星期天回家退灶可从管理员常曦处领得一斤粮票三毛钱;在我的记忆中就没有吃饱过,中学生还是普通市民中定量最高的一族。早晨跟晚上一般是玉米面或高粱面糊糊一碗(较多的时候糊糊可以照得见人影),号称二两的窝头一个,少许咸菜,晚上有时有中午的剩菜;中午一个四两的窝头或者每周一次的馒头,隔一周大概可以吃到一次炸油饼,有时有剩余的油饼,第二天菜里面便可看到切成小块的油饼;有时候有的同学剩半拉窝头舍不得吃,带回教室在火炉(冬天教室取暖用火炉,烧煤糕)上烤着,一层一层剥着吃,那香味弥漫在教室里,诱人呀;最盼望的便是轮到给食堂帮厨或者帮食堂外出拉粮食,那可以享受到神仙般的待遇:玉米面或者高粱面糊糊让你敞开了喝,窝头可以多吃几个,甚至能吃到炒窝头,有时还能喝到飘有不少油花花的挂面汤,不是任何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必须跟生活委员关系比较好,才有可能被选派去饕餮一次,新年前不知何故我有幸被选中一次,新年礼物哟。
班主任王洪老师教几何代数,严肃、不苟言笑,显得威严;但讲课口齿清楚,简洁明了,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我原先在晋祠中学代数基本一塌糊涂,可是到二中也就一个多月吧,我已跃居全班前几名,王洪老师功不可没!可我不喜做作业的优点照旧,屡被老师批评,但是成绩好也可拿来抵挡一阵。
年轻、不太英俊但却高大且英姿飒爽的杨进升老师教语文。说来也巧,我到二中上的第一堂课,也是杨进升老师分配到二中所上的第一堂课,那节课讲的是《白杨礼赞》。杨老师健步迈上讲台,操着浓重晋南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介绍茅盾先生,他爱游戏体育把茅盾先生的“盾”读作“dui”,还给我们范读课文,那节课对我来说真的印象很深,因为杨老师在下课前教我们唱了一首歌:“走绛州”,那歌词里面的“吱嘎吱嘎哧啦啦啦奔”,全班几乎都学会了;后来杨老师几乎每节课之余都会教我们唱歌,我们学会了很多;杨老师篮球打得也很好,球场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令吾辈很佩服。
让我一开始有点发愁的是英语——我在晋祠中学初一时学的是俄语,来到二中要改学英语,甚觉茫然;英语老师韩仲书,上海人,仪表一丝不苟,发型很有特色,可能是被太原化工区以南地区的空气污染所困扰,鼻子里面常常“吭吭”的;韩老师英语板书流利而好看,在课堂上常常用“嗯哼”、“all right!”“venry good!”来表示他的满意,一直到高三都是他在带我们英语,还曾在高中带过我们的班主任;记得有几次周六没有回家,我们曾趴在图书阅览室窗户外面偷看过老师们跳交谊舞,韩teacher风度翩翩、潇洒自如,很绅士的;第一次英语测验,我只得了26分,但是韩老师表扬了我,说我从未学过英语能得到这样的分数很不错,这真的对我鼓励非常大,到期末考试我以99分的成绩名列前茅!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生物老师李松岳,印尼归国华侨,讲课幽默风趣,随处可举生活中的实例,让你记忆深刻;最令人佩服之处则是他的羽毛球,据说曾获得过山西省羽毛球冠军,他的太太同为印尼归国华侨,羽毛球打得也极好;在此之前我只听说过侯加昌、汤仙虎,根本没见过羽毛球可以那样打,也根本不知道羽毛球可以打的那样眼花缭乱、出神入化;真长见识。
这是一所完全中学,高中三个年级共六个班,初中三个年级每年级六个班;我到二中没多长时间,不知何故,初二的62班拆散了分到其他几个班,我们班于是新添了李杰、陈海生等几位新朋友。后来转来新同学,我一看竟是小学时的好友王経;没多久又在57班发现小学好友孟宝忠,让我很有些高兴。当时认识了60班米天贵,却还不知道他就是儿时的玩伴贵贵。
初到二中住宿在“二分院”。二分院位于晋源南街一条叫“仓巷”的小街,是一座两进大宅院;里外院各有东西厢房共八间,外院有南房,东侧是门道,西侧角落是女厕所,内院正房是一座相当大的厅,大厅东侧旁角落是男厕所,57——60班的男生全部都在这大厅里的大通铺上睡觉;周日至周五每晚下晚自习后,从校门涌出包括跑校生在内的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由东街向二分院开进,蔚为壮观,但若是遇见下雨,那可就苦不堪言了;当时晋源城内本就很潮湿,由于地下水位较高,挖地一尺便可见水,排水极为不畅;街道也不是现在的柏油路面,土路遇水便成泥泞,街上没几盏路灯能亮,又很昏暗,走在这样的街上三步一滑,五步一跤;当时刚刚学过浪淘沙北戴河,便有同学信手拈来:“大雨哗哗下,满地泥渣,浑身泥水惹人笑,奈何远在二分院,怎样回家?”颇具曹植七步之范吧?在二分院住不过半年,记忆却是蛮深刻的。熄灯前的嬉笑打闹是必修课,57班周立莹常被王文搞些恶作剧,或者年龄大些的同学如张智、武福庚等便讲讲七侠五义、小五义或者讲些瘆人的鬼怪故事,听了会吓得睡不着,但还是忍不住要听;一旦熄灯,嘈杂声渐歇,多数同学睡着了,又从寂静中生出另外一些声音来:厕所的门“格吱吱吱吱……嘭!”,停一会儿又重新反复,如是循环不止,联想起鬼怪故事中的恐怖情节,吓得用被子蒙头不敢伸出来;上厕所是万万不敢的,只能用脸盆解决;刚刚在韩宝堂、王志成的咬牙声中朦胧睡去,突被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惊醒,深夜听到声音如斯,谁不毛骨怵然?原来是王荣做恶梦,睡靥住了,王荣个子虽高,身体单薄,神经衰弱,脸上甚少血色,夜里常常做噩梦大叫着惊醒别人,自己仍在呼呼而睡,后来到高中很少出现这种状况,许是血气旺了些;那是个极好的人,后来家传加自学,办了个中医诊所,悬壶济世(去年聚会听说他已仙去,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只比我大一岁呀)。此后许多年,我都会时不时的梦到在二分院的某些片断。
在二分院盘桓半年许,集体搬回了校本部,是被征用或是被原房主人索要不得而知。乔迁至大成殿后面、女生宿舍院前脸东西两座大厅,我们住西大厅,我跟韩宝堂比邻而眠;时值深冬,即将举行期末考试了。
考试结束,即将放假,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五斤大米,我也有一份,对我来说这可是意想不到的惊喜!因我是新转学来的,还没参加过校农场的劳动;音乐刘老师自编的一首歌中唱到:“…….颗颗稻谷赛黄金,黄金哪能年年长?”都是校农场三百亩水田打下的,听说大成殿一多半的地方装着稻谷,足足有几十万斤!校农场是之前六、七年间高我们几届的师生们在晋源城东几里许奋战数年开垦出来的稻田,为此二中还曾排演过一出歌剧《荷花盛开晋阳红》,在全市巡演取得极大轰动;此后每届学生每年都要轮换去农场劳动,农场年年丰收,每年寒假前都要给学生分大米以资过年,尤其在这饥馑岁月,白花花的五斤大米真称得上粒粒赛黄金哟!当时市内的中学曾有顺口溜曰:……学习好的到五中……,破七中、烂八中,爱劳动的到二中……云云。还有的版本如是:……想吃大米到二中……。
大米分到手,假期退灶还分得三两油,三十斤粮票,明日该打道回府,今晚怎能消停?不做点什么对不起这五斤大米呢;两位年龄大点的男生,(好像有一个是武福庚,另一个记不大清楚了)给几个人分派任务:两人去找我们打饭用的脸盆,两人去找咸盐,我跟另外三个人被派去菜窖偷白菜。
菜窖在校北门外教工宿舍北面,很大,里面堆满白菜,有一个人在外面放哨,我跟另外两人进到菜窖里面,也不知是天冷还是害怕,我身上发抖,上下牙齿敲击的“咯咯”作响,也不敢拿白菜,他们两人各抱了两棵白菜向外跑,我也跟着跑出来,回到宿舍,才发现我的背心都湿透了,任务完成。咸盐有了,脸盆没有找到,没办法就用我们自己既洗脸又解手的脸盆,去茶炉房洗干净、烫了,拿回来在火炉上焖大米(每人出一把),煮白菜,每人倒出来一点油,等白菜煮好后,烘了油泼上去,还在焖好的大米上泼了一勺,夜宴正式开始;记忆中那是初中阶段最美味的一顿大餐!真是满嘴流油肚儿圆哪。初三放寒假时又如此这般一次,但远没有这次那么香了。
次年天快暖和时,参加了一次劳动,初中全体到西山汾峪沟,学校的基地背萝卜,来回得有十几里地,回程时跟陈海生相跟,天近午,艳阳高照,还没出汾峪沟口就饿得头晕眼花了,好在我们书包中都有萝卜,没水洗,掏出来用袖子擦擦就啃,到乱石滩口,每人吃了三四个,白萝卜这东西,虽然肚子填满了,可越吃越饿,胃口就像猫抓一样难受,好容易回到学校才吃了饭。从那以后,看到别人生吃萝卜,我胃口都要难受。
63年升入初三,学校的情况有了些细微的变化:二十几位当时为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设的“红旗班主任”要调离学校了,据说是学历不达本科,他们都是专科毕业;(后来文革时期大字报中揭露是修正主义分子为了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学校而把他们赶走了,真假不得而知)我知道的有田骏、王凤贵,我们的班主任王洪老师也要调走了,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红旗班主任;下面的照片是我们送王洪老师的合影:
中间两位靠左面的是王洪老师,另一位是杨进升老师
记得好像杨进升老师代理了一段班主任,后来是郝中月接任;郝中月,北京人,北京口音很正宗,年岁比王洪老师大,新调入二中的,据说曾是军队团级干部;讲课虽说不错,但语言比较啰嗦,婆婆妈妈的,没王洪老师那么干脆,听他的课有时会厌倦。
63年春天第一次参加农场劳动,翻地,过去在晋祠翻稻地用铁锹,现在用砍嶥,我个子小,没劲,跟我一样个子小的还有方宪人、韩宝堂、张振中、迟德勇,每次砍下去只能翻起来一小块,进度也跟不上别的大点的同学,但我们依然很尽力;稻田水没有放完,残留的水淹进鞋里,冰凉刺骨,没几个人穿雨鞋,鞋都湿透了,难受的很,却没人敢叫苦,概因劳动态度在当时是政治表现中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对在晋祠小学就开始参加劳动的我来说,虽然力气小,却也能适应;后来几次劳动如:硐地(平整泡透的地)、打秧(把育好的稻秧苗拔出,为插秧做准备)我都是驾轻就熟,俨然“老农民”了。
初中时还有一个小故事:初三那年冬季征兵,我们59班好几个同学报名参军,王经也报名了,他母亲闻知,从王家坟赶到学校,死活不让王经去参军,又哭又闹还生病,我们男女同学十几人陪着她在王凤贵老师的办公室折腾了一晚上,王经终于屈服;其实当时还没有检查身体,能不能去还两说呢;后来不记得是哪两个同学参军走了。
63年夏参加了中考,那年是第一次把毕业考跟中考合并,当年秋被录取到二中高十班;从高一班到八班都是每年级两个班,我们之前的一届只招了个高九班,到我们这届一开始也是只招了一个英语班,有比我们高一届后补习一年初中学俄语的如温爱珍也在这个班,一个多月后扩招了十一班,大部从市内招来,是俄语班,女生尤其多,温爱珍便去了那边。当时从二中考到重点校三人,59班的杜耀文、迟德勇考到五中,60班的李明福考到六中,李明福是晋源东街人,后来因身体原因又转回到二中。
十班从二中初中升上来的(包括晋源当地人)约有一半强,另外从市内中学考过来的也有将近一半,有十三中的、铁一中的、三中的、一中的、九中的等,又组成一个新的集体,女生少(只有九人)男生多。
第一任班主任是杨振发,山大中文系毕业,听说在学校是反右积极分子,学生时期就入党了,我们都有些敬畏之心;第一堂课就给了干部子弟戴宝宏一个下马威,什么原因记不清了,反正是连训斥带挖苦还捎带家长,把戴宝宏训得抬不起头来。
高中头一学期几乎是浑浑噩噩过来的,作业照旧不做,课堂上看小说;到期末考试,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四门不及格,英语也才70多分,这可是创纪录的,似当头棒喝,我惊愕了,没想到聪明如我也会考不及格,其实上课根本就没听讲,课后作业都不做,高中的课程怎么可能应付得了?奋起直追吧,可怎么也赶不上了,真应了现在的一句话:输在了起跑线上。直到77年恢复高考,复习物理,力学、加速度、重力加速度,数学立体几何、还有韦达定理等等一概稀里糊涂,最后报文科了事,达线了,还因政审不合格没录取,这是后话。
在二中记忆深刻的当属文体活动和农场劳动。
高一第一学期我个子不高,体质弱,到第二学期便开始跟着康太生跑步,早上天刚亮就起床,绕着晋源城跑半圈,并做其他身体基本素质的训练,每天如是,不到一年,效果凸显:伴随青春发育个子窜到1米75,长了十几公分;肩膀宽了,速度、弹跳、力量和耐力都有长足进步,新年前夕学校举办的越野赛,我居然拿到第四名,一鸣惊人啊!紧跟着在校运会上获得跳高第三名,(杨海生第二,岳峰第一,高度一样,只是试跳次数我多一次),一下成了体育范云德老师注意的目标,后来入田径队,接受比较正规的身体素质训练,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市运会十项全能比赛;从小学起就喜欢打篮球,但因个子小身体弱始终没成什么“气候”;高二时,学校新来一位化学老师张一士,据说在天津市联队打过球,那篮球打的,说出神入化一点都不过分,看过张一士老师打球才知道篮球原来是这样打的;渐渐地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学便有意模仿张老师打球的风格:个人技术娴熟、注重战术配合,神出鬼没、指东打西,传球狠、准、快,上篮假动作多且空中停留时间长,我从中受益匪浅;当时校篮球队不收我们,我们组织高三联队(校队除外)跟校队挑战,把校队打得大败后,范云德老师便把我们全吸收进校队,直到后来我到煤矿参加工作,还是矿代表队主力队员,担任组织后卫,每年好几个月不用下井,只是打比赛,矿际的、市里的、外地来比赛的,还去过外地比赛,工资照发,能有这样待遇都得益于在学校从张一士老师那里所学的那点篮球知识。当时全国都兴起乒乓球热,我们教室前面就垒了几个水泥球台,每到下课就挤满了,王玉川、米天贵、闫旭都是打得很不错的,但到我们高二时,高一新生中有一位叫杨杰的,是山西省少年亚军,见识了他打球,才知道什么叫打乒乓球,什么是专业水准—以前所见打乒乓球,都只能称作是玩。
因了小时候有些音乐方面的天资,初三时开始学吹笛子,并考上了学校的文艺代表队,到高中时又学会了拉二胡,我跟刘柱生都在学,无形中成了竞争对手,暗中较劲,我们班课余时间就多了一些笛声琴声,以后还曾几次外出参加市里学生文艺汇演;老师中杨龙生老师二胡拉得好,曾向他请教过;卢景文老师小提琴拉的特棒,常常给我们拉二泉映月并讲解,后来调到化二建担任军乐团指挥,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老师;化学张广良老师黑管吹得好,初三时给学校运动会做发令枪纸炮火药爆炸,不幸被炸掉三根手指,以后再也没听到过他的黑管声,那时无论新年联欢会还是周末老师们举办舞会,都是这些老师在伴奏,多是些怀才不遇之人;二中地处郊区,比较偏僻,教学质量也不算很高,是太原市教育界的流放地,常有些有历史问题、家庭问题、政治问题或无甚背景但很有才华之老师被配送来此,除前文所提到的外,还有物理老师赵宗上、体育老师梁尔宁等;高一时,学校新来一位语文老师张仁,每晚在宿舍吹笛子,听他吹笛子,我才明白以前吹笛子都不得要领,无论从气息、指法,到对作品的理解、表现,根本就没有入门;学校里大部分学吹笛子的都去拜访过张仁老师,我更多次登门求教,不惜牺牲周六回家探母的机会,进步是显著的,渐渐地在学校的文艺体育方面我已小有名气,文革前报名参加中国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获得复试资格,可惜由于文革开始,取消高考,永远地失去了机会;我们十班,不管文艺还是体育,处处走在前列,运动会、越野赛自是每届的团体冠军;别看十一班女生多,文艺汇演、歌咏比赛每次都被十班打败;曾来过一批山大实习生,实习之余教我们班跳舞,叫“毕拉尔的节日”,蒙族舞蹈,四男四女:男生有团支书周世琪、班主席李杰、范楠、郎圻,女生倪萍萍、王爱桂、盛巧玲、谭素英,(团干、班干占大多数),这个舞蹈要男女生手拉手的,在那时确实是开了新风了,现在我还记得那旋律;十一班排的“井冈山上采杨梅”、“登上公社进天堂”、“杨梅酒香过重山”虽然也都不错,却还是处在下风;十班所唱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条大道在眼前”,气势磅礴、恢宏,深得评委老师好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后,我们更是学唱了许多其中的歌曲,课前、课间每个班都会响起歌声,此起彼伏,一派繁荣的校园文化景象。
说实在的,当时下午课外活动直到晚饭前那两小时,大部分学生都活跃在操场上,打球的、踢毽的、跑步的、校田径队训练的、活动量相当大,尽管当时生活稍有好转,但对于刚刚开始发育,步入青春期的这些学子们仍然是饥饿时候比较多,就那样,没有几个人会因为饿了退出活动,现在还很怀念那段生活;提到踢毽子,要数李瑞芝踢得最好了,平时她比较内向,不吭不哈的,踢毽子可让我们大开眼界,从小到大看踢毽子都是很普通的踢法,像那种“过海踢”她能够连踢十几二十个,不但踢得很高,花样还挺多,我们班很多人都学着她那样踢,我到后来也能踢二十几个“过海”,而且是左右开弓的。
校农场劳动是每学期的必修课,差不多累计“学农”近一个月时间。春种(翻地、硐地、打秧、插秧)、秋收、割稻、脱粒、打场几乎都干过,那些城里来的同学干农活儿显然要比我们这些“老二中”笨拙了许多,常被我们笑;升入高中后好像没有再分过大米,许是因为生活好转,没那么饿了吧。除了农场劳动,还常常要参加当地生产队的田间劳动,那时刚刚提出学工学农学军,我们正好是实践者,远的去过南瓦窑、近的就在东街、北街生产队,基本是水田作业,好像只割过一次麦子;曾参加过东街生产队的“反封建补课”,斗地主时,那些贫下中农们打被斗者的耳光,很响亮,我们这些学生娃大多心惊肉跳,回学校组织讨论时还要大赞贫下中农的斗争坚决,表示要认真学习之。

二中的越野活动相当普遍。晋源城西不远,乱石滩过去就是西山、汾峪沟,沟口不远是太山,学校常组织去那里进行登山比赛,不用说夺冠的总是十班;深入沟里左转向南到师家峪,沿崎岖陡峭的小路登上去便是晋祠悬瓮山后的马坊山顶,其下就是天龙山,学校组建的男女登山队,常常从这里登山;因有这样雄厚的群众基础,66年初夏,太原市组织有省体工队参加的登山比赛,我们女将们一举夺得冠军,男生们也进入了前三名,在二中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毛主席畅游长江之后,全国上下掀起到江河湖海去的热潮,二中所在晋源周围水很多,最著名是北边几里许的晋阳湖,几乎每周我们都要去晋阳湖游泳,二中的游泳队参加了市里举行的横渡晋阳湖比赛获得名次,我就是那时学会的;黄宗燧是我们班乃至全校游得最好的,广东仔,游泳自然是极好的,他爸是省农科院的水稻专家,时任省委书记的陶鲁笳专门点名从广东要来的。
一日晨,正准备起床去跑步,忽觉床板大晃,令人难以直立,上午从广播中得知原来是邢台大地震,周总理都去了;按上级要求,所有住校生都住进了学校大礼堂避震,当时是打地铺;第二天学校组织去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参观瞻仰,下午正当解说员在解说时,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感觉地面上下晃动,后来才知道是邢台地震中一次最大的余震;
在与大自然的抗衡中,人的力量多么渺小,这是我从这次地震中悟到的。
文革那段历史不堪回首,不谈也罢;值得欣慰的是十班的同学不管身处何派、什么组织,没有任何一人参与作恶,在传统教育下成长的我们实在是做不出恶事来的。
记忆中的二中,虽不是什么著名学府,甚至在中学中也籍籍无名,古老的文庙斑驳破败之处甚多,教室也大多陈旧,但她依然是我们可爱的母校;我们在那里度过的岁月美好而值得留恋,我们深深怀念那段时光,皆因为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的少年与青年时代,美丽火红的青春万岁!
后记:都说我们这代人爱怀旧。其实怀旧并不一定是怀念多少特别美好的东西,究其原因,只因为那些岁月我们正处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们深深地怀恋青春自是极其自然的。
山西忆旧之校园往事系列:
1966年的北固碾,那群躁动的少男少女